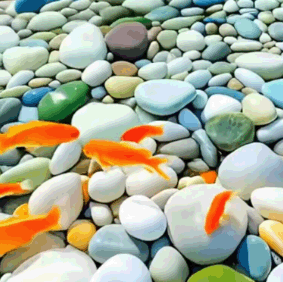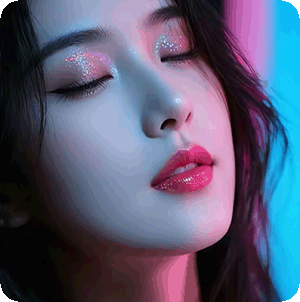6种撩人姿势,让男人无法...
在性生活中,大多时候都是男人在主动,不管是在前戏中还是性爱中。其实,女人如果在性爱中偶尔主动一次,就会让性生活的质量变得大不一样。尤其在前戏中,如果女人主动的话,只要摆出几个简单地撩人动作,就会让...

老公留着口水自摸着偷看女...
好色,貌似是男人天经地义的事
晚上十一点多了,老公迟迟没有回家,等得我心急如焚!我打老公公司里的座机,也是无人接听。由此看来老公并没有在公司加班,肯定是出去了;再说了,这么晚了公司早就没人了。接...

在性生活中,大多时候都是男人在主动,不管是在前戏中还是性爱中。其实,女人如果在性爱中偶尔主动一次,就会让性生活的质量变得大不一样。尤其在前戏中,如果女人主动的话,只要摆出几个简单地撩人动作,就会让...

好色,貌似是男人天经地义的事
晚上十一点多了,老公迟迟没有回家,等得我心急如焚!我打老公公司里的座机,也是无人接听。由此看来老公并没有在公司加班,肯定是出去了;再说了,这么晚了公司早就没人了。接...

女人必会的主导性爱姿势 性爱姿势一、背向式: 他躺下,双脚伸直,头下放一个枕头以让他能看到动作进行。你跨坐他身上,面向他的腿,手掌着地以作支撑,当你扭动时,由他抓紧你的大腿或臀部。 优点:你...

背后体位法及其应用 背后体位法与正常体位法相同,只不过女性是趴着。男性则和正常体位法相同,用手将自己撑起,从女性背后将阴茎插入。由于插入的角度问题,使得性运动不是很顺畅的进行,但引发异于面对面体位...

简单介绍下,我二十四,男朋友二十六,我们是一个公司的,去年认识后他追了我几个月,我们就在一起了,我们都是对方的第一个,第一次都给了对方,关于这个第一次,说起来至今都觉得惆怅,不知道啥滋味,就没了。...

一旦女人感到兴奋,你就可以继续这个她喜欢的抚慰动作,这会让她达到更高的兴奋程度。 男人必须记住:在抚摸女性器官的时候,要不断地变换方式。不要一直使用同一根手指,应该要换别根手指试试看,然后再使用...

肛交的正确插入指南 肛交在绝大部分女性的愿望列单上排名都比较落后,因为大多数女性仍把它看作是禁忌的体位,而且觉得使用这种体位做起来会很痛/会染上些恶心的东西/最糟糕的是她们会受到粗暴的对待。但这...

一场性爱,或许不能200分钟。但用点心,你可以拥有这10处的200次亲吻:纯真的额头、晕红的脸颊、可爱的鼻子、发烫的耳朵、微噘的嘴唇、温暖的手心、柔转的颈部、起伏的背脊、怀温的胸部、燃烧的性器、天...

快三十了,我至今还未婚。虽然谈过几个女朋友,都无疾而终。多次失败的爱情已经耗尽了心血,感觉不会有爱情了。表嫂32岁,结婚已经7年了,和表哥结婚的时候,我也去了,第一次见她,就被小表嫂的美貌惊呆了。那时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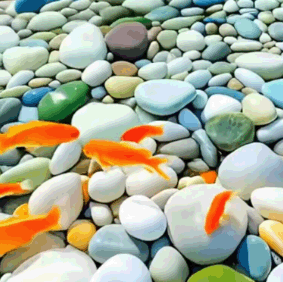
背后体位法及其应用 背后体位法与正常体位法相同,只不过女性是趴着。男性则和正常体位法相同,用手将自己撑起,从女性背后将阴茎插入。由于插入的角度问题,使得性运动不是很顺畅的进行,但引发异于面对面体位...

出轨就象吸毒,开始的时候会难受,可用不了多久就会上瘾,上瘾后你的神经会一次比一次变得麻木,你只有不断寻求新的刺激才可以保持愉悦,回想起经历过的那些年那些女人那些人妻那些情事,或许正应了那句人不风...

哥哥出差了,临前他让我每个周末回家看看嫂子,需做什么事让我帮点忙。
下午正和嫂子吃饭聊天,女友打电话非要我去陪她买衣服,我拒绝了,为此,在电话里和我大吵,我说了分手就把电话关机。本来我就不喜欢她...

那晚后,我还是每天给性感少妇帮忙。但不同的是,我们会找机会在一起亲密。我知道这样不对,不合伦理,但我们谁也停不下来,只能这样心甘情愿地沦陷下去。 4年前,堂嫂回家乡生孩子,我代表父母看望堂兄...

曼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,一个真正的女人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。这次也是在深夜,她跑过来说:“走吧。去吃点东西。”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“天下一品”的拉面馆,一碗热气腾...

“大姨妈”是每个女性的亲密朋友,现代的女人来月经有卫生巾护垫,古代的女子可没有这么幸运。那她们来月经是怎样的措施解决呢?据说在原始社会只能用干草树叶来擦拭。下面就为你解开从古至今卫生巾的演变秘密...

二十三式最基本的性爱姿势,生动的对我们性爱时所用到的性爱姿势做了一个概括。 最基本的二十三个性爱姿势。 一、羊上树 女性站立,男性站在女性前面,用一只手托住女性的臀并将女性一条腿抬高,把玉茎...

我们是住在一大栋私房里,房屋占地面积200平米,共四层半。一层停车,我和老公及孩子住在第二层,令客厅也设在第二层。公公婆婆及小叔子住在第三层,厨房在第三层,吃饭也第三层,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房子是空着...

哥哥出差了,临前他让我每个周末回家看看嫂子,需做什么事让我帮点忙。
下午正和嫂子吃饭聊天,女友打电话非要我去陪她买衣服,我拒绝了,为此,在电话里和我大吵,我说了分手就把电话关机。本来我就不喜欢她...

两性生活,是夫妻离不开的。在以前日本有所谓体位法四十种。那些原本是相扑的基本动作,演变成性行为的基本形式,再附上趣味的称谓,使得性行为充满了想像力。只要彼此愿意用点心思,由基本型式可以衍生出无数的...

我们是住在一大栋私房里,房屋占地面积200平米,共四层半。一层停车,我和老公及孩子住在第二层,令客厅也设在第二层。公公婆婆及小叔子住在第三层,厨房在第三层,吃饭也第三层,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房子是空着...